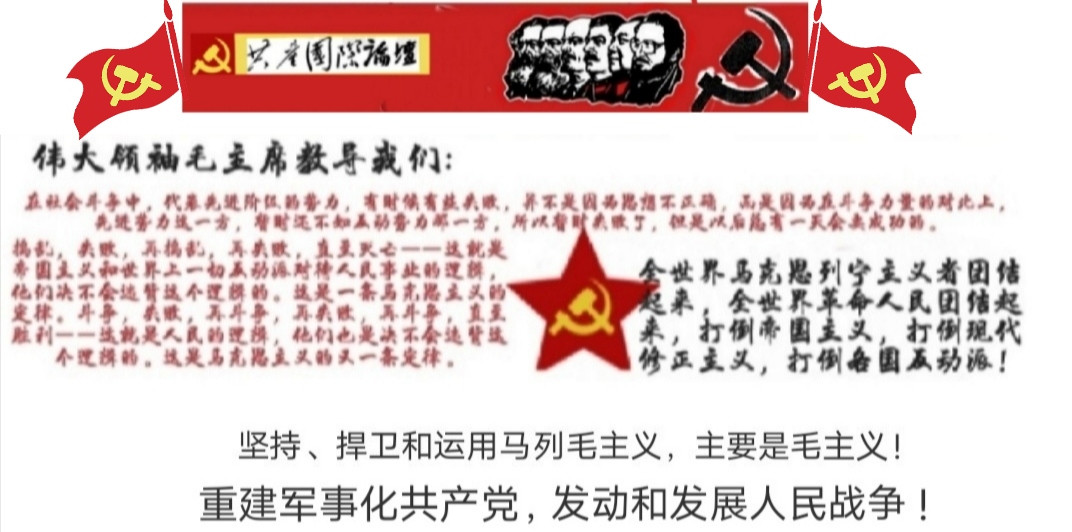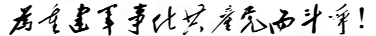转载自“工农兵大道”
托洛茨基是联共(布)党内和第三国际时期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炮制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的首脑,是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另建托派第四国际的罪魁。历史事实让我们给托洛茨基下了这样的定义,可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注定对他们的斗争是不会那样顺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帝修反疯狂压制的时候,死而复生的各路托派显得无比猖狂,他们大言不惭,说他们的“先知”是这样厉害(什么“红军之父”啦,什么“十月革命真正领导者”啦…),又是那样冤枉(什么“被斯大林派人暗杀”啦…),他们也有模有样的学着他们的“先知”来夸夸其谈他们所谓的“革命”和“共产主义”,欺骗了不少人,他们的共同手法就是抛开历史事实不谈,用诡辩论把形“左”实右发挥到极致,并无耻到将帝修反编造的用来污蔑革命者的蠢谈当历史,大有“托”平地球之势……这使我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聚焦在他们的老祖宗托洛茨基身上,我们就来简要梳理这段历史(具体的我们在前面国际共运简史系列中有阐述)和隆重介绍一下托洛茨基的几篇著作吧(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们可愿意去认真看一看呢?),我们会发现,托洛茨基的许多反动言论往往利用一些革命词句作伪装,如果不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托洛茨基反动集团的整个言论、活动而孤立起来看待,很容易鱼目混珠。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不高,时间仓促,从选材到编排,错误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当时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右倾机会主义,即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在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时候,掩盖着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托洛茨基主义。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己经声名狼藉的时候,混进苏联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就改变手法,以极端“革命”的姿态,抛出了他反动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口头上拼命鼓吹“不断革命”,实际上是不断取消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词句外衣的另一种修正主义思想,就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
同志们注意了,机会主义头子在不同的情况下改头换面,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出现的规律性现象。但他们的目的是不变的。他们总是妄图把革命群众引上邪路,从内部来瓦解共产主义运动。

列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出身于俄国埃利萨弗特格勒(后改名为基洛夫格勒) 市郊的一个富农家庭。青年时期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思潮的影晌,曾经参加过反对沙皇的活动。1898年被捕,流放于西伯利亚。1902年逃往伦敦,参加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工作。1901年至1903年间,托洛茨基曾标榜自己是《火星报》的拥护者。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秋天,他开始暴露了机会主义面目,同年底,成为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从那时起,他朝三幕四地动摇于自由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抄袭个别字眼和响亮的词句,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反对列宁主义。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进而堕落为孟什维克取消派。1912年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清洗出党、形成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时,他已不在党内。这时他打着非派别组织的旗号,大搞派别活动,另行建立反党联盟。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的革命高潮时期,他又进行政治投机,表示悔过,又归附于布尔什维克党,并窃据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十月革命胜利后还窃据了人民外交委员(外交部长)和人民军事委员(国防部长) 等要职。从此,他利用自己在党内所窃取的那部分权力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罪恶活动。伟大导师列宁逝世之后,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更加肆无忌惮。1926年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1927年被清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在国外,托洛茨基死不改悔,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40年8月,托洛茨基被其党徒杀死于墨西哥。

托洛茨基一生所贩卖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货色呢?
托洛茨基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托洛茨基说:规律“是预先预备的,而且包含在钢似的公式中的”(见《文学与革命》)。他把人的思想看成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的东西。 他还说:“一般支配特殊,定律支配事实;理论支配个人经验”, 是他的“哲学的人生观的基础”(见《托洛茨基自传》)。他否认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否认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从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他形而上学地规定了自己政治活动的原则。他说:“社会革命的激进主义--是我整个的内部生活之永远的枢纽”(见《洛茨基自传》)。这是托洛茨基经常披着革命外衣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想根源。
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史观是唯生产力论。
托洛茨基认为: “无产阶级专改不是秘密地‘夺取政权’,而是已成为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的政治统治。”“假如没有生产力的增长那就谈不上所谓社会主义的问题。”(见《苏俄之前途》)从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托洛茨基否认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俄国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
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路线是所谓“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声称他的“不断革命”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的” (见《不断革命论》。一是所谓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这个“不断性”,实际上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 “可以直接把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日程”;因为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营垒”,农民是没有革命性的“落后的一帮”,只有“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见《<不断革命>论》)。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仅要立即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立即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样民主革命可以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起完成,从而成为“不断革命”。可见他所说的“不断革命”,恰恰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否认革命的阶段性。这种“左”倾空谈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单枪匹马地冒险蛮干,实则是破坏革命、取消革命!
二是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这个“不断性”,实际上是要一步登天,一下子建成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进行, 否认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无产阶级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且“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 (见《不断革命论》)。可见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就是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民的小私有制同时一起剥夺,而且还要用比对资产阶级更加彻底的办法来剥夺农民。这种谬论的要害仍然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结果必然是破坏工农联盟,从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一种形“左”实右的反动谬论!三是所谓世界革命的“不断性”。这个“不断性”,实际上是否认各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他认为:既然农民是反动的,无产阶级在国内找不到同盟者,那么,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只有把革命推进到其他国家去,得到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直接援助,才是出路。他说:“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前提”(见《不断革命论》)。如果世界革命不能同时胜利的话,那么,哪一个国家都不要带头去进行革命。显然,这是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号,从根本上破坏世界革命、取消世界革命!
贯穿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的一条黑线,就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否认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力量,这表明他与鼓吹农民反动性的拉萨尔、考茨基之流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极右实质。他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剽窃了“不断革命”的词句,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蛊惑人心。
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路线是分裂主义。
前期,托洛茨基主张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在一个党内共处并组织各种大小集团的理论。 后期,他鼓吹极端民主化的理论和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论。托洛茨基鼓吹这些“理论”,都是为着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团结。
在实际活动和作风上,托洛茨基大搞阴谋诡计,大耍反革命两面派。他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姿态来歪面列宁、污蔑列宁、妄图以托洛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他背着联共(布)中央,招降纳叛,组成托派反党集团;他采取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等手法攻击斯大林等同志,妄图分裂联共(布)党;他甚至策划暗杀和暗害活动,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党夺权,在苏联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后面赫鲁晓夫上台后托派可谓是拍手称赞,无不认可)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先知”的几篇著作的庐山真面目吧: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是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之一,包括他在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大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所写的两篇文章:《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和《现在怎么办?》 (写给共产国际六大的信)。这两篇文章全面地攻击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系地阐述了托洛茨基自己的所谓“不断革命”的谬论,历来被各国托派的徒子徒孙奉为“基本文献”。
文章写作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伙们的反党反列宁主义活动,已轻被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彻底粉碎了。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党徒已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共产国际赞同联共(布)中央的这个决定,撤销了托洛茨基作为共产国际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托洛茨基心有不甘,在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前夕,写成了这两篇交章,向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妄图为自己的罪行翻案。

托洛茨基在第一篇交章中首先针对共产国际六大准备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什么这个纲领实行的不是“国际革命的路线”,而是“民族改良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它不是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体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这一整体出发,而是“从自己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的。他认为以自力更生为方针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以孤立发展经济本身作为目标而和世界经济断绝联系”的,在这情况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将不是一种“以国际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轻济,而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按自得其乐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组成的一个联盟”。他认为,既然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质的矛盾,那么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条件下,就只有等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摆脱这个根本性质的矛盾”,苏联经济的落后也只有在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援助下才能克服。强调只有先进国家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极革命,苏联“才会走上其正的社会主义建没的道路”。
托洛茨基在总结经验以制订新的战略方针的幌子下,攻击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把那个时期世界各国革命的失败都归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同时吹嘘自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预见”。
托洛茨基对联共(布)的攻击则集中在《现在怎么办?》这封信里。他认为联共(布)“党内有势力集团”正在“和一切阶级和平共处”。污蔑当时党组织已蜕化变质、已官僚化,说什么“党的机构的许多环节已经同国家官僚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里的富农经济结为一体”,如此等等。

托洛茨基还评述了二十年代的民族革命运动,并且特别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所谓中国革命的教训和前景,对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作了种种的造谣诽谤,污蔑广州起义“是领导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竭力否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胡说中国在1911年已经过了“二月革命”,因此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中国的“土地革命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在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相互敌对”要比俄国当时“更加不可调和”,只能建立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的反帝斗只在于取“关税自主”,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而一且成功,就意味着中国"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
托洛茨基的这两篇文章曾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散发,井为大会所否决。当时参加大会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托派分子却奉为至宝,带回国内后立即在1929年公开发表。中国的托派分子曾翻译出前一篇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一章,收入他们编译出版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并且拿托洛茨基的这些论点来作为反对当时我们党的“理论依据”。

本书是托洛茨基1936年写的。1939年中国的托派分子根据英文本译成中文,以《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为名出版。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在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经过对反对派分子的激烈斗争,到三十年代中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不但各国进步人士,即使某些资产阶分子,也为这些成就所震撼。苏维埃国家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这一切同时也都说明反对派分子的进一步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就打算用这样一本全面污蔑当时苏联内政、外交、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书来挽回自己的影响。托洛茨基在这里尽量贬低苏联当时取得的成就,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把一切罪过都推在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身上,认为十月革命已经“被背叛了”,苏联的党和国家已经蜕化,除非再过一次“革命”便无法加以挽救--这就是托洛茨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托洛茨基在本书中提出一些理论观点,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例如:
托洛茨基反对在建設社会主义时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他说, “无产阶级在剥夺资本家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把自己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时期”。如果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国家已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就必须“扔掉国家这件紧身衣”,因此“加强专政是毫无意义的事”。他不能想像,“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而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人还能同‘小投机商’和‘诽谤者’一道来推翻无阶级的社会”。
托洛茨基硬说“一国社会主义论”并非列宁的理论,它的主要理论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是列宁发现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而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上世纪就知道有这种规律,而德国的机会主义分子福尔马尔在上世和八十年代就已指出过。认为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妄图建立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为地割断苏联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建成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在本书中继续发挥他的所谓“不断革命论”。他认为“战胜谁这个历史性问题,是不能在国家境界以内决定的,国内的成功和失败只不过是为这个问题在世界舞台上的解决谁准备或多或少的有利条件”,而“如果世界无产阶级处于消极状态,那么,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导致一种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因此,托洛茨基仍旧把苏联的前途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以为这将唤醒苏维埃群众的“独立精神”而起来斗争。
对于苏联的经济政策,托洛茨基特别攻击农业集体化,认为“集体化的真正可能性......决定于工业供大规模农业以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当时苏联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迅速集体化便具有“经济冒进性质”。他说由于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结果,已在农村中培养出一批“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拖拉机手等都成了“农民贵族”。
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托洛茨基极力鼓吹党内派别自由,说什么“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不容许搞派别活动的说法,是堕落时期的话”。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不应该禁止派别活动,否则就是把国家政治制度用于党内,结果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成了“党内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托洛茨基在这里提出的各种观点,无非是他在二十年代的争论中以及过去说过的种种论调的翻版,但是在这里表达得此较集中,也更加露骨。

本书包括托洛茨基有关“不断革命”论的两部主要著作:一是托洛茨基自称为早期“论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著作”《总结与展望》 (1906);一是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驱逐到土耳其后写成的《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的主要理论。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修正和否定。它在俄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时而表现为冒险主义,时而表现为投降主义。尽管它经常披着“极左”的外衣,妄图欺世惑众,但仍无法掩盖其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本质。

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托洛茨基就一再强调,当工人阶级尚未成为民族的多数;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未合成一体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民主主义专政的领导权,无可争议地属于资产阶级。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暴露了他同列宁之间的分歧,并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定下了基调。(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当年的操作和上面如出一辙。1927年“八· 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1905年托洛茨基正式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论。在这以后,在民主革命和杜会主义革命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等一系列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严重的分岐。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和由此产生的论战,直到列宁逝世,一直没有间断。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被压迫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策略上,又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托洛茨基重新搬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论,从各方面攻击“一国社会主义论”,实际上是攻击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这场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托洛茨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被彻底粉碎了。尽管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理论上被驳得体无完肤,在革命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可是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死抱住它不放。《不断革命》一书,就是托洛茨基以论战的形式为他的这个不断破产的“理论”涂脂抹粉、百般辩解的代表作。
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他的“不断革命”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构成的,这就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实际上,有些思想,例如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问题,托洛茨基过去并没有明确说过,在《不断革命》一书中也只是提了一下,并没有作系统的充分的阐述。

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列宁在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斗争中,曾经对这大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做出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这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掌握领导权,把农民作为可靠的同盟军,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从而使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把民主革命比作第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比作第二步,主张尽快地走完第一步,然后向第二步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就是列宁加以发展的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
但是托洛茨基却从“左”的方面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并且解释,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而“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着要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各项任务”。这样,“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所宣杨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革命发展的不断性”。列宁明确地指出,“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指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问题,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以后,“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于是它“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而“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愈明确、愈坚定,它的立足基础也就愈狹窄、愈不稳”。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主动把革命推行到其他国家去,从而激起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按照托洛茨基的逻辑,“社会主义建設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斯大林同志批驳托洛茨基的这种谬论,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有共同的利益,只要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策,就完全能够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进行杜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国际革命的“不断性”问题,托洛茨基断言,社会主义是在一国“开始”的,但不能在一国“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无产阶级国家只要是处在孤立的地位,最后必然会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国的革命不是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他硬说什么世界性分工、苏联工业对于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于亚洲原料的依賴等等,这一切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事,而企图在民族范围内实现济的所有部门的完全平衡,就是寻求反动的空想。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它在一国的舞台上开始,应当立即扩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然后迅速地发展到世界的舞台。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什么“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错误在于抹煞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重大意义,否认在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因而它不是发挥而是限制那些有可能单独突破资本主义战线的个别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它不是推动个别国家无产阶级积极进攻,而是要他们消极等待“总爆发”的时刻;它不是在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间培养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精神,而是制造担心“万一别人不来援助”的犹豫心理。它的错误在于不相信一国无产阶级有条件并且有能力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西欧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上面,因而在世界革命延缓到来的情况下,或者过渡到“革命的”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立场上,或者滚到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立场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实质上是一种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词句伪装起来的取消主义和投降主义!

托洛茨基还在书中多处妄谈我国的革命问题,吹嘘他的“不断革命”论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他看来,“在中国,从1911年以来,已经没有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已经同资产阶级剥削化学地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土地问题所占的比重”是无足轻重的,无需经过民主革命的阶段。这就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要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他还别有用心地歪曲我国当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借此攻击斯大林。并且胡说,“落后的中国”没有可能“在自己民族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
托洛茨基的这些荒谬的论点早已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科学论断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驳倒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问题都做出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早在1937年毛主席谈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就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主席还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如果,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就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白不过地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

同志们,托洛茨基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在许多国家都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追随者和鼓吹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他们以托洛茨基臭名昭著的“不断革命”论为武器,否认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事实,反对工人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反对在一定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统一和纪律,要求党内派别活动自由。托洛茨基主义的披着革命外衣的特点,使它在一部分缺乏革命坚韧性的怀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的群众中和缺乏革命锻炼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历史上,各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托派集团和托派思潮严重地破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了伟大的胜利。这场斗争,是一场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得彻底胜利,托洛茨基主义遭到彻底失败而结东。历史上是如此,可想现在以及今后托派妄想对抗马列毛主义而要上演的丑剧和他们的可耻行径不但具备了失败的可能性,而且简直具备了失败的必然性,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最后,我们附上一些资料供同志们参考学习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极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极本身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土申诺的倒戈分子”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 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极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种错误对托洛茨基来说不是新的错误。它是托洛基茨在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线的极显著的特点。
低估农民在资产阶极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错误,从1905年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别明显,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托洛茨基。
——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极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象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
——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指斯大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伯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当时托洛茨基根据他的“不断革命论”提出不妨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托派在国际上接受帝国主义的赞助和支持进行反革命勾当),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