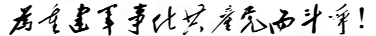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坚持胜利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性任务中,必须保持十分的自觉性,这个转变没有半分自发性可言,否则就会产生复辟的危险。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不干了,而是自己干。它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变革,无产阶级决不使国家机器—这个镇压机关更加完善而是彻底摧毁它,这也要求革命必须是在灵魂深处进行的,是要彻底解放人的思想。
修正主义者走资派们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可群众自己一组织起来,却又要想尽办法地将群众往后拉,以免自己包办替代的路线受到破坏,以免这条路线下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破坏。现在因为群众思想上的一些混乱,便有人跳出来说国家应当由少数的精英统治,群众全都是愚民。然而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也完全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过去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群众证明了,群众和愚蠢是绝对沾不上边的,群众完全能够拥有自己管理国家组织生产的能力。

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48周年的日子。纪念毛主席的最好方式就是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继承毛主席的革命遗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毛主席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成果,它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发展到了马列毛主义这个新的高度。这项理论的核心,是指出了社会主义是残余的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的共产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每时每刻都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当中,又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蕴藏在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中。最重要的一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是革命群众组织,它是群众可以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明证,是消除脑体差别、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乃至于是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前身。从革命群众组织这里就能窥见共产主义社会的影子,共产主义并不神秘。
群众组织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出现的,它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地下时期就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列宁对此进行了重点论述。在一个矛盾尖锐的帝国主义国家,革命之所以还没有爆发,就是因为群众没有组织起来。列宁说:“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像是坐井观天’,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怎么办?》)因此,革命家的任务就是去组织群众。群众组织的形式很灵活,如列宁所说:“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怎么办?》)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形式,总是把群众“撮合”到一起,形成一张熟人网络,使得哪怕最底层的劳务工人都能了解到整个企业的运作情况:从工厂中的生产,到办公室中的流通,再到上层的资本游戏。对于一个臃肿的金融企业,他的所有者——资本家,因为完全脱离生产,于是对于企业各处的情况鞭长莫及,工人组织则恰恰相反,他们在企业的基层扎根串联,于是反而比资本家更加了解整个企业的情况,乃至整条产业、整个社会的情况。革命的力量就来自于这种组织,无产阶级要依靠这种广泛的组织在举行暴动以前就成长得比资本家和政府强大得多,在革命以前就已经把整个社会牢牢地攥在手中,唯有这样,革命才不依靠任何偶然因素。
在列宁那里,群众组织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的,所以这种组织还只能作为自在的阶级,而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群众的自发斗争总是局限在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狭隘界限之内,只知道争取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劳动时长,不知道只有夺取政权才能彻底推翻剥削制度。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怎么办?》)所以,必须由政治先进分子组成工人阶级先锋队,并由先锋队来领导群众,并对群众进行政治灌输。 这种政治灌输的步骤包括:组织群众进行组织活动;系统性的政治揭露;长期斗争的锻炼。只有长期地致力于这些群众工作才能使群众突破自发性的狭隘界限。列宁说:“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怎么办?》)
“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毛泽东《矛盾论》)随着资产阶级专政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党群关系也就要求发生变动。首先,如果干部对企业、对社会实行“一长制”管理,就很容易对群众实行“管、卡、压”,使干部从人民公仆腐化变质为剥削阶级。 再加上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商品交换和分配差别这些资产阶级法权,腐化变质的干部通过利润挂帅、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就能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和货币,完成资本积累,蜕化为党内资产阶级。恩格斯说:“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共产主义原理》)毛主席更是直接点明:“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党内资产阶级搞起复辟来威力最大,这就是因为他们掌握国家机器。这一切在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以及赵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很清楚了。所以,社会主义要永葆青春,就必须突破“一长制”这种管理结构。
其次,教育、文艺、报刊等等一切宣传工具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被改造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机器,它们广泛地促进了马列毛主义的大普及,这就为群众突破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狭隘眼界创造了条件。 以上海文化大革命为例,上海革命造反工人在1966年11月组织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要对上海市委展开夺权,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立马抛出经济主义的毒气弹,提出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麻痹工人斗志,并通过煽动群众进行经济斗争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强占公房。“工总司”的工人们就识破了走资派的诡计,他们先后写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对经济主义展开大批判。在《紧急通告》中,工人们指出: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是为了: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文汇报1967年1月9日《紧急通告》)
这种群众对于经济主义的自发批判是共运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是无产阶级可以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明证,这也使得群众组织掌握政权成为可能。
随着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结社运动要求的不断发展,法律法规也就被推动着发生变革。 1966年底,上海“工总司”成立后,原本上海市委制定的“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否认“工总司”的合法性,于是工人们欲乘火车到北京告状,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11月11日,张春桥同志前往安亭同工人谈判,赞成“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组织,并签订了“工总司”代表们提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的签订,首次从条款上落实了工人结社造反的合法性,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现今可以称它为“安亭宪章”。 再到后来张春桥等同志主持修订出了1975年宪法,从宪法层面上承认了工人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这些伟大的历史成就既给我们未来的革命积累了经验,也正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的法律”。
政治挂帅是建设革命群众组织的一项根本原则,而这就靠先锋队去做引导。 革命群众组织虽然具备了政治觉悟的萌芽,但这绝不意味着群众的政治意识已经十分成熟了。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错误倾向仍然是广泛存在的。任何自称的“革命先进分子”如果打着“反对包办代替”的名号放弃列宁的政治灌输原则,任由运动的领导权被机会主义者窃取,实际上就走上投降主义的反动道路了。实际上,在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薪酬,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条件的正确约束下,是可以把干部的腐化变质限制到最小的,这些无产阶级的干部就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江青、张春桥等同志就曾在组织群众、组织写作、同群众谈判等工作上挥洒了大量汗水,这才把许多群众组织拉上了正轨。如果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群众自发性的局限性就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并因此提出“立即取消先锋队”,就又犯了崇拜自发性的幼稚病了。
民主集中制是建设革命群众组织的另一项根本原则。 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打着“集中”的旗号反对民主,还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反对集中,本质上都是走资派抛出来阻挠革命的烟雾弹——前者是官僚主义者打压革命的借口,后者是走资派分裂群众、挑起群众内斗、并妄图将群众逐个击破的阴谋。过去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最狡猾的阴谋之一,就是挑动群众组织分裂武斗。正如列宁所说:“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以,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要实现大联合,消除宗派斗争,批判“唯我独革”的思想,要让所有革命造反派拧成一股绳。 毛主席对此说道:“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历史上“工总司”在实现大联合上走在了全国前列。据“工总司”成员黄金海在其回忆录《十年非梦》中的描述,1966年11月6日在讨论“工总司”名字的会议上,王洪文同志首先提出:“上海工人组织起来后别像北京红卫兵那样,出现三个司令部,应该加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市的各“造反战斗团”通过“工总司”民主集中进行决策,决策一经通过,各“造反战斗团”就统一行动。大联合的实现,一来使革命力量有了质的提升,二来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武斗、内斗,三来把混入群众中的敌人暴露出来了,四来还促进了群众破“私”立“公”观念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诞生过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的功能几乎涵盖了一切社会领域:
一、造反战斗团、造反联络站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如前所述,各单位(例如工厂、学校等等)分别组织成一些造反组织,一般叫做“××战斗团”,当走资派窃据他们单位领导权时,这些造反组织就起来夺权。在不同单位的造反组织之间,由“联络站”进行串联,再联合形成“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形成系统性的、有纪律的组织,对市委、省委等大型国家机关进行夺权。在夺权成功以后,“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作为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造反组织如同巴黎公社那样选举出受信任的工人代表参与到政权中。毛主席在196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造反组织是众多群众组织中最具有政治进步意义的,它推动了政权结构的变革,并理应是更长时间内国家消亡的基础。
二、工人管理小组。 在鞍钢宪法推行以后,工厂内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奠定了脑体差别消亡的基础。工人成立管理小组,负责集中全体工人的意见,解决生产中的管理问题、技术问题、财政问题等等。夏尔·贝特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中描述道:“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的制定。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正式采纳。工人划分为小组,仔细、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由此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产、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这带来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广泛交流,而管理小组则作为沟通的中间人。”而在干部那边,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既防止了干部腐化变质,又使干部熟悉了专业技能,还促进了干群关系融洽。毛主席对此强调:“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三、理论小组、批判组、写作组。 经常查阅文革文献的同志会发现,文革期间大量书籍和报刊文章的作者是“××工厂理论小组”、“××大学大批判组”、“××大学写作组”,这些书籍的内容涵盖政治、哲学、经济、文化等等。这些组织是群众响应毛主席“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号召而成立的。这些组织一方面促进群众学习理论,另一方面要写文章、写大字报对社会上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大批判。根据1975年7月北京市委宣传组报告,北京全市工农理论队伍有25万人;到1976年1月,全市办起了10958所业余学校,有241.3万多社会人员参加政治学习,这种程度的全民政治是任何一个自称“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设想的。
四、群众专政小组和群众专政指挥部。 群专小组和群专指挥部是响应毛主席“砸烂公、检、法”的号召而形成的负责公安工作的群众组织。原本公、检、法机关被走资派所掌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镇压群众的刽子手。谢富治1967年8月7日关于砸烂公、检、法的讲话中提出:“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专政。……公安部的地位要把它降到一个普通勤务员,现在讲的勤务员实际上权力还是很大,要当真正的勤务员,什么人都可以领导、指挥,权力很小,象芝麻大那么一点。……北京大体上是按照这样做:是群众扭送的多,公安机关抓的少。”于是各单位分别组织群专小组,配备枪支、管教及看守等人员;全市的群专小组串联起来形成群专网络,由革委会下设“群众专政指挥部”统一领导,下设集训队。遍布全市的群专网络使得敌人无以遁形。公安机关要发挥其专业技能协助群众,一旦群众中出现坏人,群专小组就在专业公务人员的协助下自己把坏人揪出来,再由群众自己扭送至派出所。按照早年“枫桥经验”,被揪出来的坏分子并不是直接由公、检、法机关判决、处罚,而是要开群众评审大会,在评审会上坏分子和群众展开公开大辩论,以理服人,这种方式一方面利于对坏分子的改造,一方面又提高了群众的理论认识。
五、工人宣传队、农民宣传队。 工宣队和农宣队是负责管理学校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是从经过夺权运动锻炼过的群众组织转变而来的。最早工宣队和入农宣队入驻学校,是为了制止少数学校的武斗现象。到了1968年夏季,姚文元同志在毛主席指示下写作并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发动工人阶级接管教育,从此工宣队和农宣队开始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毛主席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转引自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和农宣队主持学校的斗、批、改,在理工科大学推广了“校办工厂,厂带专业”的制度:工厂中既有教室又有实验室,学生们在工厂一边劳动、一边上课、一边还能进行科学实验。教师队伍采取有实践经验的革命工农、革命技术人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一方面,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农民、技术人员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另一方面,原有的教师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参与劳动,边改造、边使用。
六、革命民兵。 革命民兵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民兵的组织不严密,革命性不强,到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民兵有的偏保守派,并且一冲就垮了。另外一边,已经掌权的造反派工人为了巩固政权,提出了成立武卫组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同志首先在上海开始试点建立以造反派为基础的工人武装。这种工人武装与两广地区群众夺解放军的枪不同,它是由上级部门按计划开展的。一开始,这种工人武装叫做“文攻武卫指挥部”,工人们只是徒手或者拿一些棍棒进行训练;再到后来,工人们编队成团或者师进行训练,先发练习枪,再发真枪,到后来一些机要部门甚至配有高射炮。这种革命民兵一方面能在反革命组织进攻时进行反击,另一方面又能在有武斗发生时随时出动,制止武斗,维护城市秩序。就上海地区来说,到1973年3月,上海总共武装了85.6万余产业工人,拥有各种轻武器2.4万件,高炮324门;建立了10个武装基干团,18个高炮团,5个独立高炮营,3个高射机枪连,1个摩托团,还有工兵、防化、通讯、雷达等等。这种革命的民兵在当时被毛主席认为正是军队改革的方向。
七、科研小组和四级农科网。 与“解放哲学”类似,群众的科研小组解放了科学。以农村为例,四级农科网就是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群众科研组织。四级农科网的“四级”分别是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和县,在这四级上分别设一些大小科研站,组成基层科研网络,这个科研网络扎根在农村里,以工农兵为主要力量,他们攻克生产中的化肥、杂交、生物防治等问题。而专业的科研人员也深入到田地里,和工农兵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河南为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80%的县建立了农科所,有70%的公社、50%的大队、40%的生产队建立了农业科学实验站和科学实验小组,参加四级农科网的人数达到110万余。仅1973年1月到1974年9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物理》、《化学通报》,以及《科学实验》等30多种期刊,就发表了工农兵写的文章140多篇。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文艺小组,工农兵们与专业文艺工作者相结合,创作诗歌、散文,发表在《朝霞》等杂志上,并在平时组织文艺演出,这使得文艺从“上流社会”解放出来;再例如赤脚医生,他们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在专业医务人员的培训下从事基层医疗工作,大队有卫生室,社有医院,使农民们都能在家门口看病,这使得医疗服务从“城市老爷”那里解放出来……种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可谓百花齐放,数不胜数。
上述这些例子中都能看到结合制这个基本结构,这对于革委会政权来说尤为重要。既然群众组织对于自发性的局限性有所突破,而先锋队的职能又还不能被完全取代,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就应当形成群众组织与先锋队相结合的政权,这个政权是党和群众的矛盾统一体,这个政权在过去就是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实行三结合:群众组织的代表、旧的革命干部和部队三结合。毛主席说:“一定要(三)结合。……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在群众组织这边,通过选举代表参与到革委会中,这一部分正同巴黎公社一样;而在革命干部那边,还要严格地集中,还存在委任制。这种结合制政权并不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不能允许打着“三结合”的旗号千方百计地把走资派、工贼等等牛鬼蛇神拉进革委会里来,应当保证革委会内干部和群众代表同心协力、相互信任,使得革委会处于一元化领导之下。
革委会中的党和群众组织,作为矛盾的两方面,自然要发生相互转化:随着群众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群众组织就担任了越来越多的本来只能由先锋队担任的职能,而干部又在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越来越融入群众。于是,群众组织这一面逐渐扩大,先锋队逐渐彻底地被群众组织所取代,国家机器也就趋于消亡了。 正如列宁评价巴黎公社那样:“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国家与革命》)在更高级的阶段中,连选举撤换这一具体的民主制度本身——作为一种僵死的形式,或者说“法权”——也要趋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群众的联合意志的直接表达。
但是,历史上的革委会制度也表现出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就表现在部队这一构成。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地区的民兵都尚不成熟,革委会中部队这一角色就主要由解放军担任了。而当时军内存在大批保守派,上至叶剑英、林彪,下至韦国清、赵永夫,军内可谓乌云笼罩。在部队入驻革委会后,这些军内走资派就勾结未改造好的旧干部,把群众组织从革委会中排挤出去,革委会的结合制就逐渐名存实亡了,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要汲取这一失败经验,就要充分重视革命民兵的建设,使得革委会的军事力量也实行结合制——正规军和革命民兵相结合,它们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并最终走向正规军的消亡。 列宁说:“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种民兵有百分之九十五将来自工人和农民,它将真正表现出绝大多数人民的理智和意志、力量和权力。”(《远方来信·论无产阶级民兵》)这种工人武装将来在地下革命时期就已经组建起来,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就应当继续成长,甚至在中央也设有相应的民兵代表,他们为中央的左派同志提供支持,这样也就不至于使江青、张春桥这样的无产阶级干部受到孤立和排挤。
随着革委会中先锋队的职能趋于消亡,而群众组织走向成熟,脑体分工就逐渐消失,工人不仅从事体力劳动,还以革命群众组织为载体参与各种创造性事业,于是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德意志意识形态》)。工友们不仅每天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共同参与政治活动、社会治安、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哲学批判等等,工友之间不只是同事关系,而且是战友关系,这种战友感情比亲情更亲,再加上家庭赡养、抚养、家务劳动也都社会化,于是家庭也就逐渐趋于消亡了。随着这种群众组织的范围越来越广,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它们将彻底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是这种战友关系的延续和深化,每个人的一切活动的社会化程度达到更高的程度,以至于整个社会能够当作一个人来看待。马克思对此形容到: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
这种联合体中,亲密战友关系的建立也正是实现按需分配的基础。过去的工农红军,哪怕经济条件十分艰苦,党内军内也实行供给制,没有薪资,这靠的就是大家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关系。分配方式的转变,本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转变,如果没有亲密的战友关系为前提,哪怕生产力再发达,按需分配也只是空谈。
伴随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带来的,同时还有“必然王国”的终结。 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其社会发展存在历史必然性——资本社会要发生经济危机,帝国主义要爆发战争,这无论是被统治阶级还是统治阶级都无力改变。但是到了无阶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本来就只是人与人之间特定关系的体现——就如同联合体的肢体的一部分一样,它改变这些社会内容就如同一个人移动他的肢体一样简单。于是,必然王国终结了,自由王国从此开始了。从这个层面来说,共产主义社会每天都是大跃进,明日的社会面貌可能与今日不同。 但是,不仅不会有人因此被时代的快车抛弃,相反,这种变革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充分参与才实现的。
人的能动性的解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远离世俗,怡然自乐,这是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人之所以想逃离“世俗”,正是因为无力改变社会,而这恰恰是不自由的表现。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为了解放人的能动性而奋斗的。于是,我们终于能理解“政治挂帅”的哲学意义——无产阶级领导一切正是解放能动性的根本前提。 哪个阶级专政是一切问题所在,而经济主义者的“争取高薪”和修正主义者的“共同富裕”对此是一窍不通的。
工作日的缩短在争取这种解放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呢?马克思对此说道:“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缩短工作日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要使工人阶级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智力。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这是使工人阶级智力发达、体力旺盛和获得最后解放的第一步。”(《1868年8月11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缩短工作日是消灭脑体分工的基础,这一点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经济主义者对此却有自己的理解,他们把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步”当做全部步骤,于是他们的一切追求就只是缩短工作日,至于工人们下班以后干什么,只要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就行了;按照这种观点,列宁关于推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努力似乎就是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了。但是列宁却恰恰说:“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 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可见,减少被动分工劳动所应当导致的,是主动的社会化劳动的扩大。 这种主动劳动也并不是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人人从事自己的爱好”那样庸俗,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不可能象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这种主动劳动的关键在于把劳动作为实现能动意识的一个环节——今日我和我的战友们乐意改善市区的绿化,我们就去为之设计图纸、植树造林;明日我们对社会上某一风气感到不满,我们就撰写批判文章、开会决策。而最开始为这些“业余”集体活动提供平台的,就是群众组织。
在一份对毛时代工人的采访录中,工人们描述了当时义务劳动的热情:“工人的生产热情非常的高,比如说在60年前后,那时几乎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领导来劝都劝不走。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有一次连续干了24个小时,我还想干,后来领导不让,强行把我拉走了。当时这种加班加点的劳动都是义务的,没得一分钱。但是所有人都想参加,如果谁参加不了,他自己就会觉得很失落,心里面很不舒服。”(《工人阶级可以当家做主!——老工人振聋发聩的声音》)可见,“共产主义必出懒汉”根本就是污蔑。一些老工人在提到毛主席时代时常形容当时的工人是“爱厂如家”。从“爱厂如家”这个细节正能看见家庭消亡的过程。因为战友情比亲情更深,小家庭就逐渐被集体这个大家庭所取代了。
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讨论到这里其实已经可见一斑了。但是正如中修把毛主席、列宁无害神像化一样,共产主义在中修这里也被披上了神秘主义的面纱。一句正确的废话被中修翻来覆去地重复:“我们现在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也不应该预先做出规定。”于是,共产主义变成了一个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中国特色”这瓶万金油出现了,“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等等乱七八糟毫无确切含义的东西——就像勃涅日列夫的勋章一样——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这些辞藻背后掩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至少要走一百年。共产主义真有那么遥远吗?不是的,这只是中修因为兑现不了共产主义而画的大饼而已。实现共产主义,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阶级斗争、结社自由,而这正是中修所回避的问题的全部实质。
过去的中国革命首先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广泛地建立群众组织并不是这种革命的主要要求。而俄国革命也只是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帝国主义中爆发的,其群众组织的组织程度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较大。但是如今,中国是一个工业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广泛地建立了群众组织,并使得全国的群众组织通过地下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未来的群众组织一方面将具有更大的潜力,一方面又面临更艰苦的锻炼,所以自然就会造就一批更成熟的工人阶级和更坚韧不拔的组织。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群众组织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理应超过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因而无产阶级会以更大的力量、更快的步伐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去。共产主义社会并不遥远,只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共同为之奋斗,兴许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同志们都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