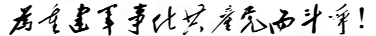斯大林无意地助长了官僚制度的发展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直贯穿着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一一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代表的反动派总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
在共产主义学说诞生时,他们迫害革命分子,他们失败了,共产主义的幽灵仍然在全世界成长。
在共产主义力量发展成长时,他们制造反动舆论,他们失败了,街垒上,农村里的枪声响彻寰宇。
在工人夺取政权时,他们端起刺刀,准备扼杀新生的政权,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刺刀被工人的铁拳粉碎。
在苏联社会主义取得初步进展时,他们用铁蹄践踏,他们失败了,红旗终于飘扬在国会大厦。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并没有消失,而一旦我们不懂得这一点,不注意到这一点,不采取措施以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那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人民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苏联的历史,深刻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先从斯大林时代讲起。
斯大林有功绩,也有错误。反动分子总是歪曲他做错的地方,因为一旦我们正确地指出他的错误,也就撕破了反动分子的一切伪装。
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没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一长制的形成与斯大林对其的发展
一长制,就是指某企业中的全体人员,完全只服从一位领导者的意志的管理制度。这个领导人由上级委派,在国家计划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企业的一切工作全权负责。
一长制最初是由列宁提出来的,列宁提出这一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而这一制度的提出,存在着鲜明的时代背景。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篇文章中,是这样描述苏维埃俄国的情形的:
最近的(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建立“协调的组织”和加强纪律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现在大家都乐意“投票赞成”和“签署”这类决议,但是关于实现这些决议需要强制,而且正是专政形式的强制这一点,人们通常却不去仔细考虑。可是,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胡说。1917—1918年的俄国,也在这方面非常明显、具体、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只有绝顶愚钝或硬不承认真理的人,才会在这方面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如果把科尔尼洛夫看作俄国式资产阶级的卡芬雅克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经过了几次非常急剧的转变而非常迅速地发展的国家,在灾难性的战争造成惨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出路。一切中间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资产阶级不能讲真话,不能说他们需要科尔尼洛夫),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马尔托夫之流的愚蠢念头(他们一味宣扬所谓民主派的统一、民主派专政、民主联合战线、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如果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进程都没有使一个人懂得不可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那么对这样的人也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另一方面,不难了解,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这些剥削者的财富,他们在组织能力上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剥夺掉的,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试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外部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内部战争即内战,而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会比外部战争造成的更大,内战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极不明确、极不稳定、极为混乱的状态。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只能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需要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群众革命热忱未能持久的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还不强大,而唯有它才能(如果它有足够的数量、觉悟和纪律)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简单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并且长期掌握政权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有害分子。
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已正确地开始实现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苏维埃组织在俄国一切民族地区的胜利进军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这个先进阶级发动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实行新的民主,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他们正根据亲身体验认识到,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
但是,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象铁,却很象浆糊。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部进行活动,采取萨文柯夫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办法,搞阴谋和暴动,以及通过他们污浊的“思想上的”反映,在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不断造谣诬蔑;另一方面,这种自发势力还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
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武力镇压转向管理工作,镇压和强制的典型表现也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在这一方面,革命群众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证明了革命的生命力,在解散资产阶级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颁布以前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即工农的法院。可是,我们革命的人民的法院还非常非常软弱。还可以感觉到,人民把法院看作一种同自己对立的衙门,这种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而留传下来的观点,还没有彻底打破。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法院正是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因为司法工作是国家管理的职能之一),法院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权力机关,法院是纪律教育的工具。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就决不能凭一时的热情,而只能靠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全民的组织和纪律来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所需要的粮食(燃料),把它们及时运到并且正确地进行分配。因此,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我们现在要最坚决反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表现在对饥荒和失业现象同组织和纪律方面的普遍自由散漫有着国民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一点认识不足,就表现在还牢固地保持着这样一种小私有者的观点: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在铁路这个可以说是最明显地体现着大资本主义造成的机构的经济联系的部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发势力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的这种斗争表现得特别突出。“蹲办公室的”人员中间产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贿者;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为纪律而斗争;而在前后两种人之间,自然有很多动摇的、“软弱的”人,他们无力抗拒投机活动、贿赂和私利的“诱惑”,不惜破坏整个机构来换取私利,而战胜饥荒和失业是要靠这些机构正确地进行工作的。
在这个基础上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赋予领导者个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展开的斗争[74],是很说明问题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觉的(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代表,想把赋予个人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作是背离集体管理制原则,背离民主制和背离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些地方利用一些人的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反对关于独裁权的法令。问题变得确实意义重大:第一是原则问题,即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人的这种做法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究竟是否相容;第二,这件事情,也可说是这个先例,同政权在目前具体形势下的特殊任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研究。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这一点上,咒骂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应声虫总是耍弄手腕,一方面,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无政府主义的、野蛮的东西,极力避开我们用来证明苏维埃是民主制的高级形式,甚至是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开端的所有历史对比和理论论据;另一方面,他们却向我们要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民主制,并且说,个人独裁是同你们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
这种论断是十分拙劣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象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象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倒退,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巨大努力,这个过渡才会实现。害了《新生活报》、《前进报》[75]、《人民事业报》或《我们时代报》[76]那种庸人的歇斯底里症的人,是不肯考虑这一点的。
就拿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来看,把这种心理同他的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比较一下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实际上从来没有看到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真正作出过任何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大的牺牲或做过有利于他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把许诺过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给他,把和平给他,牺牲“大国地位”的利益和大国秘密条约的利益,牺牲资本和利润。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当他自己用强力取得了这种东西,并且必须用强力来保卫这种东西不受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杜托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侵犯的时候,他才看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一定时间内,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喘喘气,伸伸腰和舒展一下躯体,取得一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剥削者没有给过他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当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普通的群众才能不仅亲眼看见,不仅信服,而且还会亲身感到: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会助长经济破坏,招致灭亡,导致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卷土重来。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上(因而还有心理上)相应的转变不过刚刚开始。我们的全部任务,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
资产者、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嘲笑“开群众大会”,更常常恶意地加以指摘,认为这只是混乱、胡闹和小私有者利己主义的发作。可是,不开群众大会,被压迫群众永远也不能由剥削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转到自觉自愿的纪律。开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投入新生活的行动,是他们在这样一个活动场所的初步行动,他们自己从这个场所清除了恶棍(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他们自己还希望学会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苏维埃的政权(不是别人的,不是贵族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整顿这个活动场所。正是要有劳动者战胜剥削者的十月胜利,正是要有由劳动者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指挥。
这个过渡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看到,劳动群众怎样在自己中间创造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为推翻剥削者而共同奋斗。1905年10月以及1917年2月和10月这样一些阶段,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唤醒和发动被剥削者推下去的社会“下层”,这些人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才得到了推翻剥削者、开始认识环境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的完全自由。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蹂躏得最厉害的、受教育最少的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到处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便是革命的第二个伟大阶段。
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日常劳动纪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汹涌澎群,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学会。
这件事我们一定能学会。
昨天,我们曾遇到以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杜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耶夫斯基之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威胁。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种复辟,这种同样的复辟,又以另一种形式威胁着我们,它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必须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能战胜它。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推行一长制的动机,在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还刚刚建立,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为了进行反攻倒算,鼓动社会上的一切反动分子和意志不坚定的无产阶级去以各种形式反对无产阶级政权。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用西伯利亚、乌克兰、库班的例子说明了当时的情况:**那里有富裕农民,那里没有无产者,即使有无产阶级,也是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恶习腐化了的,并且我们知道,凡是有小块土地的人都说:“我管政府干吗!我要尽量敲一下饿肚子的人的竹杠,我才不在乎政府呢!”今后,协约国将会帮助那些原来被邓尼金宰割,以后又动摇到我们方面来的投机者农民。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商业、用投机倒把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投机倒把成为国际性的。**而布尔什维克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长制的手段,用毅力,用统一的意志猛求上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工业生产,迅速恢复苏维埃俄国的元气,必须以个人独裁代表阶级独裁,用个人专政代表阶级专政的手段,去达到这一目的。这也是苏维埃政权在当时唯一的选择。列宁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用实际行动体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一长制是在一个被削弱了的贫困落后国家,一个教育程度最差的国家中所推行的。而在当时,如果不实行一长制,社会主义就有覆灭的危险。
一长制,作为一项重要的专政方式,在苏维埃俄国最初的艰苦岁月中,发挥了积极且巨大的作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承了一长制,并将它发展巩固。然而,正是这一过渡路线的长期确立,为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祸根。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对事物的分析,应该充分考虑这一事物所处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长制只是苏维埃政权在建立初期所采取的措施。这一措施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并不是永恒的。斯大林并没有很好地认识这一点,他并没有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很好地限制一长制及其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言:**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一长制在苏联的确立,使苏联的资产阶级法权更加不受限制,当斯大林意识到确立一长制的恶果并希望加以改正时,苏联党内资产阶级的阻力,已经使斯大林的努力成为徒劳。
一长制的恶果,在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时,终于显露出来了。
在同时期的中国,毛泽东为首的共产主义者看到了苏联的复辟,以及一长制所引发的恶果,1960年由工人制订的鞍钢宪法,是对一长制的进攻。而1976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一长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